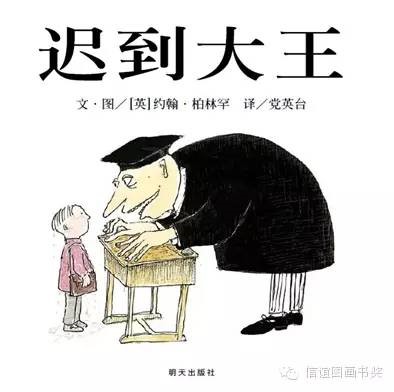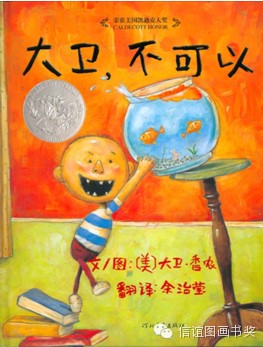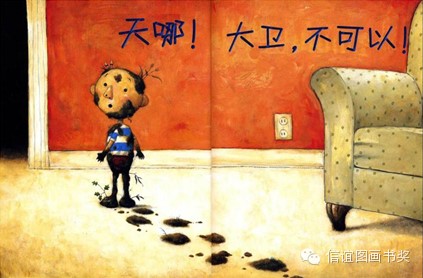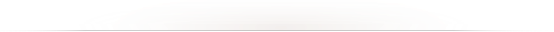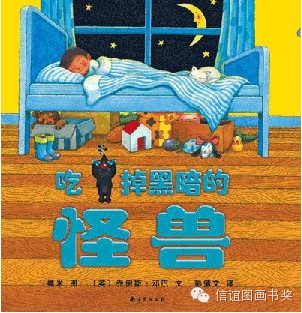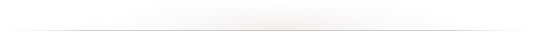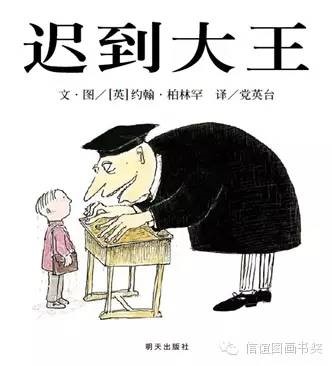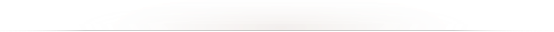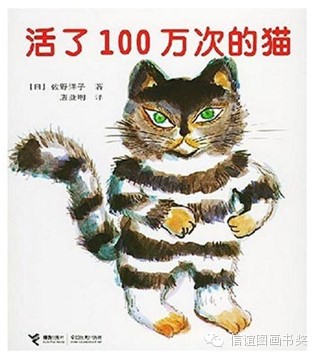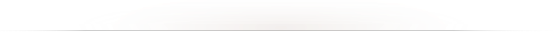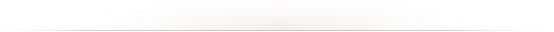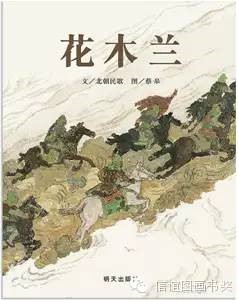|
梅子涵:我们今天谈话的题目大家都知道了,是《图画书里的儿童观》。因为我们现在讲图画书,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指的是儿童阅读的图画书,为儿童写作、出版的图画书。一本专门为儿童写作和出版的图画书,它的文字和图、它的整体面貌应该是怎样的,才符合儿童的审美、心情,才能让他们喜欢呢?让他们喜欢,同时又有儿童的图画书应有的艺术品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发展我们原创图画书的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又是非常终端的问题,是一个贯穿到底的问题。 我们今天下午参谈的这几位,都是儿童文学、儿童美术方面真正的专家,有作家、也有理论家,有画家,还有曾经是编辑的画家,所以我们今天的构成是比较丰富的。下面我们就开始谈。 朱自强:图画书中的儿童观,确确实实在中国原创图画书中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梅老师说的,问题的开始,也会一直持续,不会有结束。这样大的一个话题,用几分钟时间来谈,真的是太难了。我想说的有两句话:一、图画书是现代的文学艺术。二、儿童观是一双无形而有力的手,它在操控着图画书的创作。 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儿童文学概论》。在这本书里面,谈到儿童文学特质的时候,我觉得第一点,儿童文学具有现代性,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我自己的观点,是把图画书也归入到儿童文学的类别中来的,尽管现在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见解。那作为儿童文学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图画书也是现代的文学艺术,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现代文学。为什么要强调“现代”这个词?因为对儿童文学什么时候发生,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什么时候发生,我自己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是发生在中国整个社会化的进程之中。 以图画书来说,我觉得图画书的产生发展需要几个条件,而这几个条件都是在现代社会才能够具备的。比如说需要图画书作为商品来流通,也就是它要处在一个商品经济,我们现在叫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社会,它才有很好的发展条件。其次,要有很好的经济购买力,这也是图画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20年前我从日本带回来大概有三百册左右的图画书,我选了十本到出版社去推销,那个时候就没人要,这和人的经济购买力是有关系的,当然也还有儿童观的问题,后面我会谈。再次,就是出版印刷的技术,如果没有彩色印刷,图画书它怎么发展?如果没有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图画书可能发展的形态应该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的儿童观。如果我们在儿童观上不是现代的,而是古代的,以成人为本位的、父为子纲的儿童观,儿童文学也不会产生,图画书就更不用说了。 图画书这种样式尤其需要现代的儿童观。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看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历史会看得很清楚,越是关于小孩子的东西,产生发展得越晚。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小儿医科它在一般医学后产生,儿童哲学、儿童心理学都是在普通哲学、普通心理学之后产生的,因为关于儿童的文化,需要我们人类经过漫长时期的进化,然后当我们的智慧、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它才能更好地发展。这些能力和智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归结到儿童文学这里,就是“儿童观”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现代社会儿童观的出现,我觉得儿童文学,特别是图画书,是难以产生和发展的。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我想说的第二句话,“儿童观是一只无形而有力的手,它在操控着图画书的创作”。我这里具体地谈两个问题。我认为,儿童观在图画书中有两个表现形态。 第一,它使一个作家的创作姿态显露出来。我们在一本书的后面其实能够看到一个作家的创作姿态。比如说,我在9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的图画书里面看到过一些没有画家署名的作品。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画家好不容易画出来的作品不署名?因为他没有把给小孩子作画、做图画书当作一件值得敬畏的工作来做,他画得不认真,羞于署名。这里面就有儿童观的问题,他会怀疑小孩子有没有能力欣赏真正的艺术作品?我认为是有的。你要用适合孩子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那如果你认为,小孩子懂什么,我随便画两笔就把你打发了,那你就会画成像《大灰狼》这本图画书里,把狼画成马的样子。我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这样的画怎么敢于把自己,把艺术家的名字写上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为儿童创作的姿态这样的问题。为孩子做图画书,也需要艺术家竭尽自己的才力,否则如果你不尊重孩子审美的能力,没有正确的评价,你就会认为图画书可以偷工减料,可以降格以求。这样的作品我们过去是见到过的。 另外一点,是对儿童的心理世界、情感世界以及他们的愿望在进行表现的时候,你的表现的方式,是直接地受图画书作家的儿童观操控的。我这里可以谈一点具体的例子。柏林罕有一本图画书叫《迟到大王》,这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小男孩上学总是迟到,而且迟到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原因。我觉得这一本图画书就是反映儿童文化和成人文化之间的一种矛盾性和冲突性。它是讽刺成人逻辑的一部作品。而且我特别在意这个作家柏林罕,他和童年有非常深切的联系。因为我比较痴迷于英国夏山学校的那种自由教育,柏林罕就是夏山学校的一个学生。我读过一些介绍这个学校的书,我觉得它是一个保护童年、维护童年的地方。柏林罕其他的例如《莎莉,离水远一点》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有它的儿童观,都有它自己的站在儿童立场上的儿童观存在。
另外还有一本图画书就是大卫·香农的《大卫,不可以》,这是一个系列的,还有《大卫上学去》、《大卫惹麻烦》等。这本书读了之后,我是很受震动的。首先我们看这个画家,他和童年的联系,他用的这个画,比如那个男孩子的形象,据说就是他童年时候的涂鸦作品,然后再创造成《大卫,不可以》这样的作品。这个作品里面,写了大卫这个男孩做了很多让大人头疼的事,但是我注意到的是这个作家,他对这样的幼儿的成长状态的承认,他认为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就是这样成长的。我们都知道图画书的画都是要表达故事的,有些有意义的故事的图画我认为应该有寓意性。在这本图画书里面,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场面,就是大卫玩得浑身都是泥巴,然后走到客厅里面,他的腿上和头上,泥巴都是大块的,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泥巴上长出了小草。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寓意的,就是在作家、画家的眼里,他认为儿童的胡闹、顽皮,缺乏经验的惹麻烦、闯祸,对大人来说很头疼的这些事,都是孩子成长的养料,就像那几块大泥巴一样,都能够促进小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样的图画书,都是作家在儿童观上,不仅是尊重,也不仅是理解孩子,而是在儿童成长的生命形态里,看到了珍贵的人性的价值,孩子在这里面能够得到一种认同。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一个童话《一只想飞的猫》,这个故事是对那只想入非非,想飞的猫进行了讽刺,然后让它尝到了教训,这又是另一种儿童观。一个画家、作家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进行创作?不同的儿童观,就创造出不同的作品。我是觉得像《一只想飞的猫》这样的童话作品,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已经不被孩子所接受了。在这样的童话的影响之下,我觉得孩子那种想飞的天性,想超越生活的天性,想成长,想成为巨人的天性,都会得到压抑和束缚。我们在很多优秀的图画书里面,看到的是对孩子天性的,不仅是理解,也不仅是尊重,那里面还有解放。
方卫平:这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因为中国原创图画书正在完成它的一个启蒙阶段,或者说它的启蒙期到了它的尾声了。可是很多重大的话题究竟有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在2008年济南召开的第一届中国本土原创图画书论坛,那是第一次关于原创图画书的论坛,我记得在那次论坛上,我的报告的一个中心意思是,中国图画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来建立或者说培植自己的图画书的素养。 我们有很好的画家,可是我的想法是,从一个好的画家,到一个好的图画书,这里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来不及了,容不得我们骄傲或者说盲目乐观。因为已有的图画书的成就,对我们很多孩子来说都是新的问题。我们从插图的概念,从连环画的概念脱身出来,打量图画书这个品种的时候,我们业界对图画书这个品种的素养是不够的。我认为这次论坛所涉及的关于儿童观的话题,可能是我们关于图画书,尤其是关于原创图画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话题由这次论坛及时地提出来,我认为很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论题很有针对性。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儿童观的问题不仅是儿童文学界的,或者教育界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和公众还存在着很多误区或者认识盲点的这样一个领域。朱永新先生也讲过:“我们对童年秘密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我在课堂上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的,里面说,我们这个世界看似对儿童已经有了很多了解,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对童年有重大的误解。它举到我们大陆著名的慈善工程“春蕾计划”的例子,这是专门资助那些因为贫困而失学的女童的。春蕾计划中有一句听起来很动人的广告词“帮助一个女童,就是帮助一个未来的母亲”。我在课堂上拿这句话和同学们讨论,三分之二的同学都觉得这句话很好,很感人,只有少数同学说好像有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句话非常有问题。这句话偏偏就是把童年自身的价值,童年应该享有的、应该接受文明的滋养或者书本的滋养的权利,忽略掉了。我是因为她以后要当母亲才帮助她的,不知不觉当中,你看我们对童年的误解有多么大。像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多的。 说到童年观,如果按照我们文章的方式,首先要界定它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的确是这样,比如童年,我们对童年的了解到底怎么样。童年看待世界的方式,童年了解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的。我接触最多的孩子,就是我儿子。我记得在他二年级的时候,我给他念一首我很喜欢的加拿大诗人丹尼斯·李的一首儿童诗《进城怎么走法》,我跟他说:“这首诗非常好,我们一起念。进城怎么走法?左脚提起,右脚放下。右脚提起,左脚放下。进城就是这么走法。”这首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好,要跟孩子分享,但是他一念就说:“爸爸,这首诗有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就演给我看了,他是用动作思维的。他说左脚提起,右脚怎么放下啊,右脚提起,左脚怎么放下啊?其实这就是孩子,这就是他对语言、对世界的感受。所以其实我们对于童年的认识还有很大的误解。我讲的这是第一个我们的针对性。 第二个,我觉得对中国原创图画书来讲。我和朱自强老师一起参加丰子恺奖的评奖,我们在评委总结阶段,对两岸三地的图画书的现状和特征做了比较。大陆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它的底蕴、背景,以及作家们对这些元素的运用。那几部获大奖的作品,它里面的儿童观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可是比较下来,总体上来讲,台湾的作品在这方面会更自觉,更丰富,有更多的童趣,更加多元的儿童生活,更加民主的儿童观念。我觉得对于大陆的原创图画书来讲,除了我们要增加图画书的素养以外,怎么样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更好地引入童年的视角,更好地对童年有个尊重或者更多的呈现。像《妈妈买绿豆》、《小鱼散步》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例子。还有约翰·柏林罕的作品,比如《莎莉,离水远一点》,我觉得这个个案如果拿来分析的话,它在童年观和图画书的呈现方面,都可以让我们作为典范来看的。它充分利用图文的特点来叙事,左右两个画面讲的是两个故事,左边的画面是白底的,是成人的世界,是爸爸妈妈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右边的世界是莎莉幻想的世界,实际上它不是现实的世界。右边是没有文字的,左边有妈妈不停的唠叨,这个是第三个世界,就是现实中莎莉的世界。这个叙事的智慧给我很大的震撼。约翰·柏林罕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为儿童代言,站在儿童对大人质疑的这样一个立场。其实他的作品更加适合成人来反思。我觉得他的作品孩子们也会喜欢,像《迟到大王》这些,因为它本身反映了孩子的世界。
虽然我们在座的或者这次论坛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论坛,这个话题的提出,是非常及时,非常有价值的。
彭懿:今天我来的时候,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带来了一本《儿童文学》杂志,这里面正好看到了我最敬仰的日本作家壶井荣,她说,她创作之初并不是为儿童而作的,她当时只是抒发自己的一种心情,或者某一种回忆。所以她写出的文字被称为“越界的儿童文学”。其实她是为大人而作的,可是被拿来给孩子阅读。 这次我们论坛的题目是《图画书里的儿童观》,其实图画书中的儿童文学观,我想把它做一个分解。我想这个话题如果往小里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剥离出“儿童看”和“看儿童”这样两个问题。我想这是两双完全不同的眼睛,一双成熟、智慧又饱经沧桑,一双稚嫩天真。这两双眼睛,一双是大人的眼睛,一双是孩子的眼睛。 我先来说说“看儿童”这个问题。我觉得看儿童实际上就是一个创作者他们是如何看儿童的。我说的看和朱自强老师他们的儿童观还不一样,我想说的是,其实你透过任何一个图画书的文本,稍作探究,就可以知道文本背后的作者是如何看儿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要提到我刚才说到的儿童文学作品越界的问题。我主观而武断地认为,那些作家在写出这些越界儿童文学的时候,他眼中是没有儿童的,他们只有记忆中的自己,可是他们的作品呈现的是一种儿童生活。其实有一件我一直认为很荒谬的事情,就是《窗边的小豆豆》这部作品,在中国被认为是儿童文学作品,可是在日本它绝对不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这是一个成人的回忆录。可是我们现在说到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拿它举例。它其实只是适合儿童阅读罢了。我相信那个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也应该没有我这是要给几岁小孩看的这种想法。
我想说的问题是,图画书不一样。我们图画书的文本里不一定有孩子,也不一定是咿咿呀呀的像一首儿歌,我们的文本不一定很轻,也可能很重,重的是叙说一个具有思想内涵的哲学问题。但是我想说,创作者在写出或者画出这个文本之前,在他的视野中一定会出现一个或一群孩子的身影,不是他记忆中的那群孩子,是清清楚楚地站在他面前的孩子。这些孩子是谁呢?是他未来文本的读者。这里我想岔开一句,就像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最终评出的获奖作品很少,大部分是被淘汰的。淘汰的因素可能有很多,比如画的不好,或者故事讲的不够妙,但是我想其实有很多作品之所以没有获奖,就是创作者在创作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为谁而做的,换句话说,就是他在创作之前,没有看到那群读者。其实当一个创作者如果预先看到了儿童,在他下笔之前,都会提醒和关照自己:“我的读者不是大人,是孩子。”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我觉得一个为孩子创作图画书的作家或者画家,他们与为大人写作的作家的不同之处,不是书的厚与薄,不是内容的浅与深,而是在于他自己知道是为儿童而画的,他看见了儿童。只有看见儿童,才能像艾瑞·卡尔那样画出《好饿的毛毛虫》,也只有看见儿童,才能像芭芭拉·库尼那样画出《花婆婆》来。
其实作品的主人公是不是孩子,我觉得不重要,这本书讲的是不是一个孩子的故事,我认为也不重要。我认为重要的是,当一个创作者看见了儿童,也就是目的非常明确,知道自己是为儿童创作一本图画书的时候,他就必须去迎合孩子的阅读。其实“迎合”这个词在这两年被染上了一种不好的感觉,我想说的迎合,不是去取悦,不是去讨好,不是去巴结,不是说孩子喜欢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也不是刻意去把一个故事简单化、浅显化,甚至去降低它的思想高度。我们是大人,我们有教育孩子成长的使命,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对人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告诉孩子,告诉他们什么是丑和美,什么是善和恶。我们当然可以讲一个有思想有深度的大故事,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必须让一个孩子看懂、读懂你的这本图画书,这就是我说的迎合。 那孩子们是怎样阅读一本图画书的呢?什么样的图画书适合孩子们呢?孩子们是自己看还是听大人读?我们作为一个作者,对这些问题都不能不理不管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画出一本好书。唯有这样,我们创作出来的图画书才能让孩子看懂、喜欢并记住。 以前几米先生的书我看了很多。我们说到几米的时候,都是说“成人绘本画家几米先生”。在首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的颁奖典礼上,我听到了几米先生的讲演,他讲了怎么制作《吃掉黑暗的怪兽》这本图画书的过程。他说他以前都是做成人绘本,可是有一回英国的沃克公司要他画一本给孩子看的图画书,他觉得自己没有给孩子画过图画书,感很好害怕,不知道怎么画。这是他最感动我的一句话。现在我想想,一个一直画成人绘本的画家是不是在担心自己的创作过程中看不见儿童呢?当然几米先生在创作之时,就自始至终都看见了儿童,因为这本图画书是他与英国的老牌童书出版公司沃克公司合作的,他身后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创意总监一直在像影子一样提醒他孩子、孩子、孩子……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儿童看”。一本图画书到了孩子手里,让他们爱不释手还真是不容易。他们喜欢看什么呢?还真是让我们这些大人伤透了脑筋。有时候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孩子们会天天让你讲,月月让你讲,你不知道这个故事有什么好听。还有的时候,一幅没什么可看的画面,孩子们盯着它百看不厌,哈哈大笑。可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些让我们很感动的故事,他们连一个字都不要听。所以我想,其实最难的问题,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你要知道儿童看什么,他们喜欢看什么。 我说的都是路人皆知的常识,但是正因为路人皆知,它却更容易让你忘却忽略。所以我们这些路人,我们这些创作者,我们这些图画书的编辑、图画书的爱好者,就更要牢牢记住“看儿童”和“儿童看”了。
周翔: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一方面担任编辑,一方面又是一个作者。我今天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梳理、交流一下。儿童观的理论问题,我觉得就交给理论家来解决。我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述一点观点。 第一,我觉得儿童观的建立,从大的方面来讲,肯定是有一个能展示儿童观的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儿童观肯定是影响着图画书的发展,从欧洲、日本、韩国,乃至台湾,它的图画书发展的后面,一定是有儿童观支撑的,没有这个支撑,我觉得不可能做出好的图画书。 第二,从编辑角度来说,我觉得儿童观对于编辑是非常重要,甚至比创作者还重要。因为编辑是代替儿童来选书的,儿童不可能跑到作家家里去选书,也不可能跑到画家家里去选书,他一定是通过编辑的眼睛去选书的。编辑如果有好的儿童观,如果理解儿童,才能做出真正为孩子做的图画书。如果你没有好的儿童观,那你可能在选书时就是选的成人的图画书。就像彭懿老师所讲,我们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书可能孩子是不喜欢的。我觉得儿童观是我们编辑来挑选作品的一个风向标。回想我自己做编辑的这么多年,我一开始是很不懂儿童的,慢慢才稍微懂一点点。回首自己以前做的很多图画书,当时自己觉得很得意,觉得文字多好,画面多好,而且也得了一些奖。但是现在反过来看,那些真的不能称之为图画书,他最多就是我们成人自己欣赏的图书而已。慢慢接触到儿童观,也是看了在座很多老师的著作之后,我知道编辑心里一定要长出儿童观,长出来后,你就能慢慢走到编辑的行业里面去,那么你跟作者的交流,和你自己选书的时候,才会慢慢懂得什么是好的图画书。 柏林罕是我非常喜欢的画家,《迟到大王》我也看了很多遍,它的翻译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书名“迟到大王”这四个字,我觉得翻译得不够妥贴。实际上这里面也有儿童观。在彭老师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里面,他也讲到了。彭老师说,原来的书名叫《约翰派克罗门麦肯席,一个总是迟到的男孩》。我觉得这个书名,实际上和柏林罕的整个故事的风格是相像的,因为他磕磕绊绊地念,实际上在念的长度里面,可能已经反映出一个孩子害怕迟到或者说是幻想性的一个孩子的特质,而“迟到大王”,我觉得有点强势,好像他很喜欢迟到的感觉。四个字读起来可能是容易一点,但是它的意义或者对作者的精神,我觉得编辑和翻译者是有误解的。
最后,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或画家,我对儿童观的看法。我以前画的很多当时觉得很好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是一堵墙。孩子通过我的画,走不进故事里去。这个是我画了这么多年后,我慢慢悟出的一个道理。一本好的图画书,一定是让孩子能走进去的图画。我觉得一个画家其实是应该向孩子学习的,学习儿童想看到世界本质的心。艺术创作说到底,实际上是童年的延续。我记得《小王子》里面讲,你真的要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看不清楚的,你必须要用心去看。毕加索也讲过,他花了一段时间,学习了艺术创作,但是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把它抛弃掉,去学习儿童看世界。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无论是图画书画家或者是作家,实际上都是有很大的启示的。我们要学习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不是为客观上的所谓现在的孩子来做的,实际上是为内心的儿童在做的,因为内心的儿童是永远长不大的,他和各个时代的儿童的心是相通的。我觉得要抓住自己内心的那个儿童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作品来。 我还要再举个例子,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画家艾瑞·卡尔。最早以前我看《好饿的毛毛虫》,还是日文版的,我只觉得他画得很好,它的媒材用得很好,设计也很好,但是我没有理解他对儿童的一种看法。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艾瑞·卡尔实际上是个老顽童,他是在用这本书给孩子们做游戏,而且还做了一桌非常漂亮、新鲜、好吃的食品。他不仅用了孩子喜欢的反复的语言,还用了很多孩子喜欢的游戏方式。我觉得这是他跟孩子来对话的一个游戏的过程,包括他的食品,还有最后吃饱了说肚子好痛,把孩子贪吃的个性表现出来了。所以很多孩子读了这本图画书后爱不释手,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一定是内心里有了儿童,他寻找到他自己内心的儿童,他才能做出一个好的图画书。
姚红:我自己是从创作到阅读到编辑到教学这样的一个过程过来的。我有两个体会可以跟大家探讨。一个是关于创作者的儿童心。曾经有一位德国儿童书画家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的故事中的主角都是你儿子的名字,而且好像模样也是他,是不是你儿子的出生给你带来的创作的灵感?”这个画家他沉思了片刻说:“其实我听到儿子第一声啼哭的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我的童年结束了,我要做父亲了,我不能为所欲为了。”其实他这个话是过于悲观了,事实上他的童心不会这么泯灭的。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位褒有童心的成年人,在创作当中,他即使表现的是儿童生活的情态,也并不是纯客观的一个观察的结果。与其说是观察,倒不如说是自己童心的一种折射。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是可以带来作品个性化的,会是一个非常充沛的有童心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儿童的阅读。我是因为自己过去做过编辑,现在也有继续跟出版社的编辑进行合作。一部儿童图画书作品当中,虽然不是绝对,但是可能会存在显现的和隐匿的两个成分。显现的部分是儿童易于亲近的,好奇的,是以他们的心智发展而言,容易被点燃兴趣的情节和内容。这一部分是儿童可以自己读出来的。隐匿的那个部分,是故事背后的某种意味深远的道理,这个部分可以说是等来的,我们的导读帮不上忙,家长和老师帮他解释了也可能都不能解决问题。关于这一部分,我们的导读包括推介,可能只是在向家长或者幼教工作者指出这是一本好书,但是可能未必在当前能对孩子说得清楚。我的体会是,如果仅仅有第二部分,也就是讲人生的道理,那不是儿童读物,它必须是有第一部分作为前提。我们知道儿童对自己感兴趣的图画书是反复看的,他爱听的故事是要一遍一遍听的,这样他留下来的印记,随着自己年龄的成长会明白得更多。反之他对于内容引不起兴趣的图书,再大的意义也归结为零。 比如《活了100万次的猫》,就像金波老师说的,青年人可以读出忠贞的爱情,老年人可能会对生命价值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前面情节的选择。比如说这只猫身为一个国王被乱箭射死,身为马戏团的一个临时演员被失手砍死……种种的选择以儿童的眼界来测定都是相当有趣的。拿掉这一部分,这个故事不能成立。这一部分使孩子喜欢,反复地看,看了以后留下记忆。记忆在了,后面的东西是本来的,不是看来的。不过有些出版社编辑就会认为这个不适合儿童,因为有些意义孩子们读不懂。我觉得这个是多虑的。还有一些从事幼儿教育的,他们说儿童读不懂潜藏的意义,所以在替孩子选择的时候,就不去考虑它,他们会觉得马上就能读懂的,具有很浅的意义的才是合适的。我觉得这就有一点点武断。
我也遇到过关于安徒生童话的讨论。安徒生的童话很多人说,它比较忧伤,它有很多人生的哲理,它是为成人而写的。最近也是偶然的原因,我又看了一下,我觉得故事台前的那部分,孩子非常感兴趣,这点很重要。比如说《皇帝的新衣》,后面的裸体游行小孩子会觉得很好玩,会很喜欢。至于它背后含有的东西,你现在跟他说了也说不清,也不见得要急于说,不要慌、不要忙,随着孩子年龄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读到的自然会不一样。比如说虚伪、奉承,甚至裁缝之间合作的默契,这些东西因人而异,会读得很多的。我觉得这对我们从事这一方面操作实践的同行朋友,对于儿童阅读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前的一定要抓住儿童,台后的那种东西不要着急。有的东西是读来的,有的东西是等来的。
曹文轩:我今天想提出几个问题,就是这个题目《图画书里的儿童观》是指作者的儿童观决定了图画书的制作和命运呢,还是指图画书中显示出来的儿童观呢?第二个问题是,是指儿童儿童观,还是指我们成年人的儿童观?我以为儿童有“观”吗?精英主义者描述儿童说,儿童来到世界上只是一块白板,今天朱永新先生说,儿童的秘密有多少,我们还不知道,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叫黑匣子。那到底是白板还是黑匣子?我以为,既是白板,又是黑匣子。我是说有儿童的儿童性,却没有儿童观。儿童性是先天的,儿童观是后天的。我们说图画书怎么能使儿童喜欢,实际上是说我们的图画书怎么更符合儿童性,而不是儿童观。因为儿童是没有儿童观的。 什么是儿童性,很难定义,他大概与欲望、人类的史前意识、集体无意识等概念有关。你的书是写给儿童看的,那么你就不能忽略儿童性。但随即我们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儿童性是否具有天赋的合理性,我们可以无条件地顺从儿童性吗?我怀疑在儿童人权的名义之下的儿童至上主义。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就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是具有天赋的权力的,就是社会秩序的正常化,人类历史不断演进的一个保证以及社会伦理。所以我一直在所有的场合,反对儿童文学作家去做儿童的代言人。我曾经到学校做过讲座,我就对那些学生们讲,对老师和校长们讲,我说,校长、老师与孩子的关系,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的另外一种变体。我就对那些孩子们讲,我说:“我现在在讲台上,你们要知道这讲台是谁的。绝对不是你的,你可以走到这个讲台上来,但是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得到我的同意。”那么图画书也一样,它大概不只是顺应儿童性,同时还应具有提升的一个功能。 那又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知道儿童性吗?你曾经是儿童,就一定知道儿童性吗?儿童性是怎么被我们知道的?一个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家或者说一个图画书的作者,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个儿童性的?人类探究了这么多年,揭开了黑匣子了吗?揭开了儿童性了吗?大概没有,大概是人类永远要探索的谜。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作家确实感应到了。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也是最神秘的东西,它的名字叫“直觉”。一个作家能否体会到儿童性,这不是谁能教会的。 接下来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一本儿童观正确的书,儿童就喜欢了吗?我看不见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的喜欢不喜欢,主要是源自于天生的儿童性,而不是后天的儿童观。我们在琢磨一本图画书如何来让孩子喜欢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琢磨儿童性,而不是在考量儿童文学观。我们大概还应当有另样的绘本,那就是已经被正当的儿童观浸润过的儿童所喜欢的绘本。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绘本有两种,一种是顺从儿童性,另外一种是塑造一种更高级的阅读之范。 然后又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来确定,一本图画书是小孩喜欢的呢?是看图画书的发行量吗?一本没有足够发行量的图画书一定不合儿童性吗?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本图画书与儿童之间,特别是那些还不识字的儿童之间,他们中间是有一个中介的。也就是说一本图画书并不是直接与一个孩子发生关系的,中间有一个中介——母亲。其实我们在琢磨儿童性的时候,是在琢磨母亲心中的儿童性是什么。而且这母亲是无法摆脱功利性的目的的。比如说大家都在说的《猜猜我有多爱你》,为什么这本书发行量这么大,当然它确实是一本不错的图画书,可是那些母亲们为什么就喜欢把这本书念给孩子听,难道背后只是说这本书符合儿童性吗?大概不是。它与母亲的特别的考量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里,其实潜伏着一个问题,就是一本图画书到底是孩子喜欢还是母亲喜欢?图画书的推荐者们所面对的主要是母亲。
剩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无法真正了解黑匣子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何良策,究竟有什么办法?我在以上的一切描述里头都在说,我们谁也不要说我们了解儿童,我,还有在座的,大概谁也没有勇气说,谁也没有这个本领说,你就了解儿童。那么在如此情况之下,我们又能怎么办?我的看法是非常极端的,也是非常个人化的。这就是求助于艺术。如果那个绘本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我说的是真正的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从来就是拥有广大读者的,今天不拥有,明天一定会拥有。假如它不能拥有,它肯定不是一件艺术品。 从我写作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琢磨孩子到底喜欢什么。到了后来,我才终于发现,鬼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思路,我把力量放在一部作品的精心的制作上才发现,其实对象是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去琢磨的,因为孩子就在你的灵魂之中。这个时候,我就有了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没有艺术,哪里来的对象。 那么究竟何为图画书?我以为对它的界定宜宽不宜窄。所以我才提“无边的图画书”这个概念。既然图画书本来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上本来没有图画书,在没有图画书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也很健康。曹雪芹时代没有图画书,但是曹雪芹也一样在长大成人,而且还为我们写了一部《红楼梦》。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图画书不重要,只是说它是后来时代的产物,我赞成朱自强先生对儿童文学和儿童图画书的历史的界定。它并不是必然要产生出来的,它可能不是人类必需的,但是却可能改变了人类。我想说,它是被我们创造出来的,既然它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它的规律、规则也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许多年前,我就以橄榄球为例讲过一个道理,我说:“世界上本来没有橄榄球,不知在哪一天,被一个或者几个奇思怪想的人发明了,如果不是这几个人,人类大概至今也没有一个叫橄榄球的玩意。”橄榄球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的,人类也不会因为没有橄榄球就活不下去。假如说活得不好,那也肯定与没有橄榄球无关。橄榄球的规则同样也是由我们自己确定的。橄榄球出现了,但橄榄球本身并没有说你要怎样将我们玩耍。如果橄榄球的规则是必然的,那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橄榄球的玩法呢?我觉得图画书与橄榄球同理,它需要注意的是,它如何才能与欣赏者的认知能力大致相等。如何吸引他们,又如何提升他们。好画、好故事,意味深长,富有诗性,留下了很多巧妙的机关,可以口口相传,代代相传,可以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超越语言,超越时代……倘若如此,我们还在乎什么呢。 梅子涵:曹文轩老师用一系列的发问,把我们普通人丢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其实一切都是不可讨论,也不可知的。比如说,他一贯地劝说成年人,不要以为我们懂了点儿童。我倒想问的是,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认为我们不可知的呢?难道一个成年人就真的一点都不能了解儿童吗?我们都说世界上各种哲学一直在诞生,为什么有各种哲学在不断诞生、在发展呢?是因为各种哲学一直都在思索人类的本身,可是每一种哲学,它都对人类有一种认识。同样我们不必在认识儿童这件事情上面那么悲观。事实上一个长大的成年人,他是能够认识儿童,能够认识儿童当中的某些东西的。你认为要全部认识,那才叫认识。那我想说,如果这样,儿童自己也不认识儿童自己,我们成年人也不能认识我们成年人自己。所以我说,一个成年人认识儿童,意思不是说要全部彻底地认识了儿童那才叫认识儿童。从这一点上说,能够认识儿童的某些,这就叫认识儿童。因为认识是不可能寻求自己的,而自己的认识,是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步解决的。所以我认为我自己对儿童是有一点认识的,但是我不可能完全认识儿童,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可能完全认识。 我在想一个儿童文学的作家或者一个儿童图画书的画家,如果在你的内心,你认为儿童世界是完全不可能认识的,那我觉得你的写作已经丧失了一个基本的信心的前提。事实上,曹文轩他一直都认为他认识儿童的,因为我在他的很多文章里面都看到,他所知道的儿童就是他小时候的儿童,只是他认识的未必是今天的儿童,未必是全部的儿童。 另外,刚才有一点,就是关于儿童观和儿童性的问题。其实我理解的儿童观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作为一个童书的写作者、创作者,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的作家、画家,他应该对儿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为儿童写作的书、画的画,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比如说什么样的趣味,什么样的语言的难度,什么样的思想的高度,是可以被儿童进入的。儿童性从哪里来的呢?比如说一个作品里面充满了儿童性,有儿童观的趣味,那这种儿童性和趣味的诞生,正是来自于一个写作者,他拥有了儿童观,拥有了不彻底的局部的儿童观。他对儿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他写出来的人物和故事才能符合童真的那一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儿童性。 曹文轩:非常感谢子涵。其实他发展了我的观点,他和我的观点,我以为并不是矛盾的。其实他说的很对的,我自认为我是懂儿童的。我刚才强调了,就是你教我怎么去认识儿童,教是教不会的。我特别讲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这叫直觉。如果我不懂儿童,大概我也不可能写这么多书。其实我到底懂不懂儿童,我的书到底小孩喜欢不喜欢,出版社他们最有权发言。我说的,“我们谁也不要说你知道儿童”,这里说的你不知道儿童,也是从整体意义上讲的。你说的是局部意义上知道儿童,我说的是从本质上,指全面的,你能不能知道儿童。所以你的观点和我并不矛盾。 第二,关于儿童观,这里的儿童观我说是指儿童的,而不是指我们自己的。就是当我们后天还没有教化他的时候,他是没有儿童观的,他是没有“观”的,他只有“性”。性就是说由娘胎里带来的,所谓人这个人种他本来就具有的。当然这个到了孩子后期有了儿童观的时候,创作者在写东西的时候,可能又要进一步琢磨他的儿童观,不仅仅是儿童性了。但是我以为最初的那个孩子,很小的孩子,他是没有所谓的儿童观的,他只有儿童性,就是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就是人类的潜意识或者人类的史前意识,或者说是荣格讲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我说的天性,而不是观,观是后天来的,而不是指我们作家。我们作家当然有我们的儿童观。所以我做一点点解释。
蔡皋: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体验。我觉得我自己总是在做准备,一部作品从开始到结束后我都一直在做准备。面对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从表达、到内容、到呈现,我会花很多时间去构想它,然后表达、完成。这段时间,有时候可以说是痛苦的过程,因为否定的东西有很多,从时间上说,听起来都有点害怕,像《桃花源的故事》,花了3个年头,像《孟姜女》也是,花了很多年,废掉的画稿和构想要比成功的多得多。我这里想表达的是,我自己有一种需求,我希望我的作品是艺术的,我非常看重作品的艺术感,艺术品质,我希望我做的图画书,让孩子知道这是个艺术品。 我这种想法由来已久。最初可以退回到,我和俞理老师一起工作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我们做童书的被大家看成是幼稚的,而且不受关注的。包括现在我们有一些编辑,他们偶尔也会感慨,说自己是做不了画家才来做编辑的。我听到这样的话,会很郁闷。我不觉得给儿童的童书是不会画画的人来做的事情,或者说是随随便便可以对付的。所以我很多年以前就说,我要做艺术品,要做成很好的质量,让小孩子看到以后,会一眼看出它是好的。他们能感觉到什么样好,什么样不好,而且能看出什么样的作品它好在哪里,这又是更高的要求,需要一定的功力。所以当一些读者读到了我图画书里的好处的时候,知道了它的质地、品性的时候,我会感到由衷的喜悦,知道有了回声。我是这样对待我的书的,所以我每一本作品都会很投入地去做。 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不等于说我的图画书和孩子们没有距离。就像《宝儿》,这个作品它本身就带有成人的东西,蒲松龄的就是给成人看的。但是就因为我小时候看过蒲松龄,听过他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实现某种跨越和超越的,所以我还是做了。但是我觉得孩子们在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仍然是有距离的。所以我在最近的这些年做的事情就是大量的阅读。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要看到这么多国际上很好的图画书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还在补这一课。所以我花大量的时间在读这些文本,就像曹文轩老师说的那样,他的很多话是让我很震撼,很受启发的。原来真正的好的图画书它应该是这样的品质,并不单纯是指艺术的,它是很综合的,图画书的指向也是有多重含义的。
除了阅读作品外,我最近几年的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花很多的时间跟儿童打交道。我在跟儿童打交道的时候,我感觉到成人看的有趣,和儿童自己觉得有趣还不是一样的事情。比方说,我和我的小孙子在花园里看到小苗苗要发出来的时候,我就跟小苗苗说好些话,我说的话跟他的话也是不一样的。他跟小苗苗说:快出来吧,请不要那么害羞。我觉得他比我讲得好,他感兴趣的事情和我的不一样。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成人喜欢有序的美,我在和他玩积木的时候,我就想引导他了解有序世界的有趣,就给他搭有趣的房子,但是他的兴趣点跟我不一样,他关注的是积木往高处堆的时候能堆多高,堆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推倒。他对你盖的城堡有多好看一点也不惊奇,他喜欢的是把它推倒的那个快感。所以我从这些方面就是想说,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他的有趣是我猜想不到的。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确实也能给我很多感觉。我就在想,跟他们相处的经验会不会对我以后图画书的创作有影响,让孩子能更好地进入我的图画书,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比如说他喜欢看的一本日本的图画书,就是讲下雨天去踩水的,他也会跟着图画书里的动作去动他的小手小脚,因为这是他熟悉的东西,他对他熟悉的东西更感兴趣,我觉得这个图画书就很成功。总之我觉得唤起了他的经验或者他有感觉的时候,他进入你的图画书的时候会好一点。 我觉得很好的书应该有个引导作用,我们自己应该有种前瞻性,应该把最好的东西放在那里,等他去发现。我做的事情只是让他慢慢地去发现那些有趣或者等到他有时候再去看这本书或者对相关的问题会感兴趣。我们应该跟孩子一起去经营,让他了解这个世界,这个是过程很漫长,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就像桃花源,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但是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只要我们有心的话,还是可以做到。屋顶也可以变成花园。就像花婆婆做的那样,走到哪播种到哪,我用自己的行为去感染孩子,孩子也会反馈给我更多的东西。
从出版社出来之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学生,我真的很好奇地去读很多的书,很好奇地去做我曾经没有圆过的梦,我就是梦想当一个纯粹的画家。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时间,现在有了,我非常高兴。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最新的起点,然后孩子们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有更多这样的交流。这样的情形,让我每年都有了一本记录。我觉得这种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积累,星星点点都在那里,都是很原生态的。这个对于我创作来说,我不指望它将来变成什么东西,但是我相信它是在养育我,给我很多启发,让我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气场,让我觉得有一种活力。我觉得对于一个图画书创作者来说,这个很重要。像张执行长说的那样,蹲下身去和孩子讲话,真的去理解他们的世界,和他们交流,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像碎片一样的东西中,也会有好的像珍珠一样的,需要去雕琢的,也许它会雕琢成图画书,也许只是成为我的记录。我喜欢、珍惜这部分东西,然后等待新的契机。就像万花筒里面那些红红绿绿的东西,它们需要有个三棱镜在滚动的时候,才形成景观,才能形成迷人的图像。我就在等待碰到这种棱镜,然后产生新的作品,我也在期待。 |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